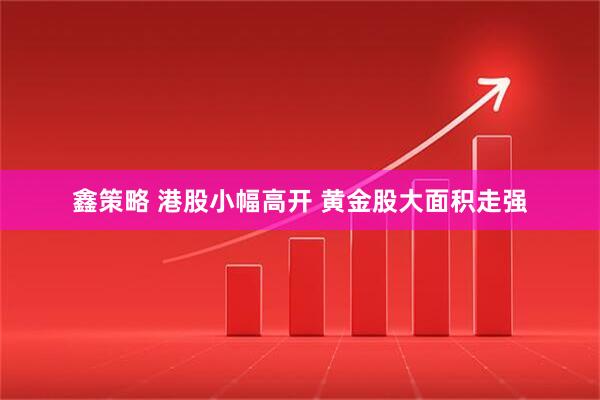西周初年,周公旦向他的弟弟卫康叔发出了一份诏书,这份诏书便是《尚书·酒诰》。其中提到了一项重要的制度——“内外服”,也就是商朝的“内外服”制度。书中提到:“越在外服,侯、甸、男、卫,邦伯;越在内服,百僚、庶尹、惟亚、惟服、宗工,越百姓、里居。”这段文字主要讲述了商朝在内外服制度中的不同角色分配,其中“服”字的本义,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像一个人跪坐并持物的形象,象征着屈服和服从的意思。具体来说,“内服”指的是商王的亲属和族人,而“外服”则多是服从于商王的异邦和诸侯。 商朝对内外服的管理力度有所不同,商王对内服亲族的命令称为“令”或“乎”,而对外服的命令则称为“比”。在甲骨文中,“比”字呈现两个人并排的形象,表达了平等的意味;而“令”字则像是商王张口向跪坐之人发布命令,显得更加单向。这说明,在商王的眼中,“内服”更具有从属关系,而“外服”则呈现出更多的平等性。值得注意的是,无论是“内服”还是“外服”,它们本身并非单纯的职官,而是作为独立的族群存在,承担着为商王家族服务的责任。 在《酒诰》里,“外服”首先提到的是“侯”。在甲骨文中,“侯”字的形象像是箭矢集中在箭靶上,最初是指箭靶,古人也将箭靶称为“射侯”。晋代的孔晁在注释《逸周书》时指出,“侯”代表的是“王的斥候”,即侦察兵或巡逻兵。随着时间推移,“侯”这一概念逐渐转变为军事长官的职务。所以,“侯服”实际上就是指为商王负责军事巡逻和防御的职能。王宇信和杨升南在《甲骨学一百年》中指出,甲骨文中的“侯某”和“某侯”各有数十位,而“侯”在商朝的外服中占据重要地位。商王武丁甚至曾派出他的妻子妇好,派“比”侯去征讨夷方。由此可见,“侯”的职能是商王军事指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而“诸侯”这一称谓,其实正是从商代外服中的“侯”演变而来的,意味着“多个侯”的合称。在周代,许多“侯”的职位本质上就是由周王分封的军事长官。 接下来提到的是“甸服”。金文中的“甸”字,由“人”和“田”组成,象征着人在田地里耕作,意思是从事农业工作。在甲骨文中,虽然没有“甸”字的字形,但有大量与“田”相关的记载,如“田武”“田黄”等。孔晁在注释时解释,“甸”即指“田”,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。因此,田服的职责便是为商王提供粮食支持。商王武丁曾派出妇妌前往“田萑”指导农业生产。此外,历史上也有一些“田服”发生反叛,甚至被商王征伐的情况。《左传》记载了晋国和曹国作为“甸服”的例子,其中便隐含了对田服的管理和控制。 再谈到“男服”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,“男”字由“田”和“力”组成,象征用农具耕田之人,也与“任”字有通假关系,因此有“某男”和“某任”的表述,例如“雀男”或“戈任”。孔晁注释时提到,“男”指的是“任王事”,即为商王从事某项职事。男服的职能比较复杂,既有为商国服务的情况,也有反叛的时刻,甚至有些男服部族曾参与对商国的进攻。《左传》中提到的郑国被称为“伯男”,也是男服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周代五等爵中有“侯”和“男”,而商代外服也有相似的职称和职责,两者之间的联系不言而喻。 接着是“卫服”。甲骨文中的“卫”字由“行”和“口”构成,象征着拱卫和保护。孔晁注释中指出,卫服即是为商王提供捍卫职能。实际上,卫与侯一样,都是承担军事职能的职务。西周初期,周朝也有一个叫“卫国”的地方,它的名字很可能与商朝的卫服制度有关,表明了周朝继承了商代的部分职制。 然后是“邦伯”。在甲骨文中,“邦”字由“丰”和“田”组成,象征着通过种树来界定疆界,意味着国家或国土;而“伯”字形似大拇指,指的是家族中最年长的兄弟,也用来表示掌权的长者。甲骨文中的“邦伯”通常指的是方国的首领,他们与商王处于平等的关系,并非隶属于商王的“外服”范畴。与“侯”相比,“邦伯”更多代表了并列关系而非从属关系。 除了《酒诰》所提到的“侯”“甸”“男”“卫”和“邦伯”,一些学者还在研究中指出了其他的外服,如“犬服”和“牧服”。甲骨文和金文中的“犬”字像狗的侧面,“牧”字则像持鞭放牛的人。“犬服”主要负责商王的田猎工作,而“牧服”则主要负责畜牧业。虽然这些外服在《酒诰》中没有明确提及,但它们依然在商代的制度中占据了一定位置,并在周代逐渐消失。 从甲骨文中的这些外服职能来看,它们的职责虽然不同,但并未形成明确的等级制度。商朝的外服制度看似职责明确,实则存在许多模糊地带,尤其是它们并非是全职性的职务。徐中舒先生曾在1955年提出,商朝的外服可以被理解为“指定服役制”,这一概念在赵世超等人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他们通过借鉴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,揭示了商朝外服制度的深层次含义。对于重构商周早期国家的剥削方式,这一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发布于:天津市万生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